
圖:甜粿。
跨入農(nóng)歷的十二月,跟住在香港的母親視頻聊天時(shí)��,母親的話語(yǔ)里便會(huì)反復(fù)提及一句話,“呀�,年節(jié)到來(lái),年節(jié)到了”�,言語(yǔ)中透著習(xí)慣性的焦慮。今天��,又嘮叨她的表姐真厲害��,這兩天蒸了九斤的甜粿要分給她的孩子們�����。
母親說(shuō)的是閩南話���,閩南話里的甜粿是年糕中的一種。閩南的年糕花樣繁多�,其中數(shù)甜粿最常見(jiàn),也最不可或缺��。母親五十歲上來(lái)的香港����,也嘗試在香港蒸過(guò)一次甜粿��,可惜廚房的灶臺(tái)太小���,爐具太小,沒(méi)有蒸成�����。環(huán)境改變了����,多年的習(xí)慣不得不放棄。有些缺憾是春天萌發(fā)的細(xì)芽��,一到時(shí)節(jié)便會(huì)冒出來(lái)�,壓也壓不下去。我明白母親的心思���,她在香港三四十年的時(shí)間里�����,每逢春節(jié)內(nèi)心涌動(dòng)的依然是閩南鄉(xiāng)下老家的情懷����。
自從她結(jié)婚,每年春節(jié)前要大張旗鼓蒸糕蒸粿�����?!笆锾鸺@、十斤鹹粿��、十斤芋圓���、十斤碗糕���、十斤地瓜粉粿……”母親沒(méi)講完,我的頭已經(jīng)暈了��?����;叵肫疬@些���,母親自己也感覺(jué)不可思議,當(dāng)年怎么有那么大的精力去完成這些。
不得不佩服母親這輩子生活在農(nóng)村的女人們��。她們似乎無(wú)所不能���,養(yǎng)育子女����、下地種田�、操持家務(wù)。閩南地方向來(lái)“信巫鬼����,重淫祀”,祭拜先祖神明�,為家人禳災(zāi)祈福,是她們生活中的另一項(xiàng)繁重的內(nèi)容�����。在物質(zhì)貧乏的年代����,她們從田地里刨得糧食,再用巧手變出各種美味的食物����。在閩南一年四季花樣繁多的年節(jié)里�,這些食物先呈予神明面前��,然后端上家人的餐桌����。正月十五的元宵圓、清明節(jié)的潤(rùn)餅菜����、端午節(jié)的糉子、七月半的炸棗�����,哪一樣難得倒她們���。她們就有這樣的本領(lǐng)�����,在廚房里蒸騰出每個(gè)年節(jié)相應(yīng)的食物,在我們的記憶里種植下家鄉(xiāng)年節(jié)固有的味道�。
每年家里都要備好糯米��,糯米是自家地里長(zhǎng)出來(lái)的���,顆粒格外飽滿。母親會(huì)先提早一天將挑好的糯米浸泡一夜�����。待到每一粒糯米吸足水分����,試著挑一小撮,用手指頭搓一下����,能搓開(kāi)來(lái)時(shí),就提到村里的碾坊�,碾成粉末。磨好的粉倒進(jìn)大大的鋁盆里���,按照比例加糖加水�,糖以紅糖為佳����,用力攪拌���。黏稠的糯米粉與紅糖與水,充分融合成米漿����。黏稠的米漿要用力去攪拌,讓蔗糖與糯米里所有的甘飴釋放出來(lái)�。備好幾個(gè)口徑大約十五六寸的圓形鐵質(zhì)盤(pán)子,在盤(pán)底抹上一層花生油����,然后擺到竹製的蒸籠上,取一個(gè)大鐵勺子�����,把米漿舀入鐵盤(pán)里��。
手腳麻利的母親一邊裝著米漿����,另一邊灶膛大鐵鍋的水已經(jīng)被煮開(kāi)了。兩三層蒸籠被架到大鐵鍋上���。一把把的粗糠往灶口推進(jìn)去����。粗糠是大米的外殼��,曬乾來(lái)就是絕好的燃料���,火苗舔著稻殼�����,發(fā)出噼里啪啦的聲響��。煙囪連接灶臺(tái)處貼著灶王爺?shù)纳裣?,在神位前點(diǎn)上一炷香���,大概連續(xù)點(diǎn)完三四根后���,甜粿就蒸熟了。黏稠狀的米漿結(jié)成了塊����,圓圓、憨憨的����。母親趁熱用刀切一小塊試一下甜度和黏度����,再反思總結(jié)一下這年做粿的所有程序���,有些不合家人口味的瑕疵待到來(lái)年得修正一下���。
一切完成得如行云流水一般。最后將甜粿從鐵盤(pán)中剝離出來(lái)��,放在簸箕上����,置于通風(fēng)處。甜粿的熱度迅速退去�,冷靜下來(lái)的甜粿逐漸變硬變乾,可儲(chǔ)藏很久���。即使發(fā)霉了也不打緊���,把發(fā)霉處切掉,甜粿的內(nèi)核一點(diǎn)也不會(huì)受影響。
整個(gè)春節(jié)的大小祭祀里���,甜粿成了供桌上的主角����。它們是神明的摯愛(ài)�����,也是我們年夜飯的一道佳肴����,吃了年糕年年高嘛���。我的三個(gè)哥哥較之父母更早來(lái)香港��,一年難得回鄉(xiāng)一兩次�,年底必定會(huì)回鄉(xiāng)下過(guò)年的���。母親憐惜在外打拼的孩子會(huì)關(guān)切地在電話里問(wèn)他們年底回家想吃什么����。得到的回復(fù)基本就是母親養(yǎng)的雞鴨和親手做的糕粿。年復(fù)一年�����,母親做糕粿的水平越來(lái)越高��。大哥愛(ài)吃甜粿�����、碗糕�����,二哥對(duì)芋粿情有獨(dú)鐘���,三哥喜歡鹹粿���。
除夕夜晚,一家人團(tuán)團(tuán)坐好�����。母親將甜粿切片����,沾上打散的雞蛋�,下油鍋炸��。本來(lái)堅(jiān)硬的甜粿���,給它們點(diǎn)溫暖�,漸次變軟���,恢復(fù)剛出爐的狀態(tài)。出鍋的甜粿片四周冒著細(xì)細(xì)密密的小氣泡�����,發(fā)散著甜絲絲的味兒����。冒著熱氣的甜粿黏性極強(qiáng),片與片間稍微一接觸立馬黏在一起���。待到甜粿端上桌�,只要其中一個(gè)人���,筷子一伸����,整盤(pán)的甜粿都會(huì)被夾起來(lái),然后�,你扯一塊,我拉一塊����,一張張臉兒在屋內(nèi)的火燭照耀下通紅通紅的。大伙嬉鬧聲一點(diǎn)都不輸屋外地動(dòng)山搖的鞭炮聲��。
過(guò)年在香港���,母親不做甜粿等年糕�����,但是甜粿之類的年糕必然會(huì)有�。有時(shí)親朋好友送�,有時(shí)自己去買(mǎi)。香港的年糕花樣百出��,除了傳統(tǒng)的用糯米制作成的年糕外��,還有用蘿卜、馬蹄���、芋頭���、臘肉等等原料制作的各式年糕。年糕經(jīng)常標(biāo)著某個(gè)大酒樓的牌子��,用精美的紙盒包裝著�����。母親會(huì)虔誠(chéng)地把它們擺在大年初一祭拜天公的桌上����。這些年糕更像身著華麗服飾的尊貴客人��,感覺(jué)與它們之間始終有一道禮節(jié)上的距離�����。
吃年夜飯時(shí)����,碰上的甜粿要么過(guò)硬要么過(guò)軟����?��;蛘咂鋵?shí)也不硬不軟��,只是不符合我內(nèi)心二十幾年反復(fù)沉淀下來(lái)的一個(gè)黏度的標(biāo)準(zhǔn)�。我當(dāng)然也不知道這年糕是出自誰(shuí)的手��。它們大概都是流水線出來(lái)的�����,大多都極工整���,邊緣絕不旁逸斜出�����,圓得異常合乎標(biāo)準(zhǔn)�。
兒子在外求學(xué)多年����,每年春節(jié)回來(lái)前�,我也是照例會(huì)問(wèn)他過(guò)年想吃什么�����。他每次都有點(diǎn)為難�����,給不出答案����。他在另一個(gè)都市里學(xué)習(xí)喜歡上了那個(gè)都市的包容與大氣,喜歡上了那個(gè)都市的女孩��。母親廚房里頭那套蒸煎炸炊的本領(lǐng)�����,我一點(diǎn)也沒(méi)學(xué)會(huì)?���,F(xiàn)在的年夜飯也簡(jiǎn)單���,訂上一盆盆菜就解決了��。然而���,我是否該努力點(diǎn)����,做一道菜����,在他的味蕾留下關(guān)于年節(jié)的獨(dú)特記憶?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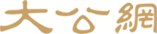


 京公網(wǎng)安備11010502037337號(hào)
京公網(wǎng)安備11010502037337號(hào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