圖:張仃上世紀(jì)五十年代創(chuàng)作的中國畫《紫砂藝人》\清華大學(xué)美術(shù)學(xué)院提供
丁酉年是誕生于上世紀(jì)一○年代的張仃先生的百年誕辰�����。這位被尊稱為“藝術(shù)泰斗”和“大美術(shù)家”的老人于七年前溘然離去����,在跨越兩個(gè)世紀(jì)的藝術(shù)生命里,其豐富性和開創(chuàng)性在中國美術(shù)史上都堪稱“二十世紀(jì)最獨(dú)一無二”(馮遠(yuǎn))���。貫穿今年全年的紀(jì)念活動(dòng)在中國的東西南北中延綿不絕����,從最高藝術(shù)殿堂到民間草野�����,又復(fù)燃了一股“張仃熱”��。盡管這位大師生前身邊總聚集著一大批文化精英和藝術(shù)追隨者�����,但對(duì)百年張仃的紀(jì)念�,仍不啻為一場(chǎng)殿堂與民間相互應(yīng)和的“對(duì)張仃價(jià)值和精神的搶救”。”大公報(bào)記者孫志
初冬時(shí)節(jié)��,“張仃百年誕辰紀(jì)念展”在清華大學(xué)藝術(shù)博物館三個(gè)展廳火熱進(jìn)行�����。進(jìn)入主展廳,絳紅色背板兩側(cè)分別書有:“中國革命文藝的先鋒”和“中國藝術(shù)創(chuàng)新的旗幟”����。前身為中央工藝美院�����、現(xiàn)為清華大學(xué)美術(shù)學(xué)院用最高規(guī)格的展覽紀(jì)念老院長張仃����。著名畫家袁運(yùn)甫說:“張仃先生的人格魅力具有強(qiáng)大號(hào)召力�。‘張仃是我們的旗幟��!’我想這是每一個(gè)中央工藝美院師生共同的想法。在他主持美院工作時(shí)期�,工藝美院就是國家美學(xué)的設(shè)計(jì)師����,他將最時(shí)尚的理念帶給了社會(huì)����。”
國家美學(xué)“首席設(shè)計(jì)師”
一九三八年二十一歲的張仃從榆林到了延安,這位集國仇家恨于一身的青年早已將漫畫視為武器���,這使得他在藝術(shù)生命之始就植下紅色基因�,這為一九四九年以后新中國美術(shù)的發(fā)展完成了別人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務(wù):無論是“包裝新中國”,負(fù)責(zé)開國大典美術(shù)設(shè)計(jì)����,設(shè)計(jì)改造中南海懷仁堂�、勤政殿;抑或設(shè)計(jì)國徽����、政協(xié)會(huì)徽、開國第一套郵票�����;還是主持設(shè)計(jì)北京“十大建筑”�����、擔(dān)綱一系列國際博覽會(huì)中國館總設(shè)計(jì)師�。一切皆為歷史造就��,一切也皆是時(shí)代使然�����。中國國家博物館原副館長陳履生認(rèn)為:“張仃在每一個(gè)歷史時(shí)期的貢獻(xiàn)��,所呈現(xiàn)的藝術(shù)精神���,無疑會(huì)成為今天文化建設(shè)的一份重要遺產(chǎn)。”
在北京西山腳下���,被稱為“大鳥窩”的張仃先生寓所—一棟藏身于樹林中古樸的兩層石頭房子����。這個(gè)“詩意的棲息地”選址于太行山馀脈,正應(yīng)了老人一生對(duì)大山的眷戀�。秋日午后�,灰娃倚坐在丈夫往日專屬的寬大藤椅里����,向《大公報(bào)》記者講述起這一年所發(fā)生的三個(gè)動(dòng)人故事�����。
美術(shù)史應(yīng)補(bǔ)進(jìn)工匠貢獻(xiàn)
耄耋之年的楊先讓是張仃最早一批美院學(xué)生����,曾任中央美院民間藝術(shù)系主任。在山東濟(jì)南的紀(jì)念座談會(huì)上��,情到深處的楊先讓落淚了��。據(jù)他回憶,建國初期剛考上美院只懂得學(xué)西洋�����,認(rèn)為中國的東西是落后的,而先生第一堂課就講書法�����,并到民間搜集刺繡��、版畫、雕塑等帶進(jìn)課堂��,這一切新中國美術(shù)教育的開拓性試驗(yàn)�����,在當(dāng)時(shí)情況下都是頂著壓力的艱辛探索�����。而此后中央工藝美院在初建時(shí)期即形成了注重繼承和發(fā)揚(yáng)民族民間優(yōu)秀傳統(tǒng)的學(xué)風(fēng)�����,當(dāng)時(shí)學(xué)院建立了泥人張�、麵人湯�����、皮影藝術(shù)工作室�,并請(qǐng)剪紙藝人、民間印染���、裝裱���、壁畫名師傳授技藝����。楊先讓動(dòng)情地說:“年齡日增才越發(fā)理解先生的美術(shù)思想:‘美由人民創(chuàng)造����,在人民的生活中傳承和發(fā)展,生生不息����。’”
南通六位彩錦繡工藝師也專程赴北京看望灰娃���。三十四年前,七十名蘇北年輕姑娘與張仃合作完成北京長城飯店《長城萬里圖》巨幅彩錦繡壁畫����,這六位正是當(dāng)年女繡工的代表��。三十四年過去����,堪稱長城飯店鎮(zhèn)店之寶��、估價(jià)已超過長城飯店本身的巨製�����,至今仍被無數(shù)游客瞻仰���。長城永在,壁畫無言�,就像是對(duì)張仃永恒藝術(shù)生命的紀(jì)念��。彩錦繡壁畫是張仃處于藝術(shù)變法時(shí)刻�����,用焦墨山水展現(xiàn)他對(duì)藝術(shù)真諦以及簡(jiǎn)約本質(zhì)的參悟����,而南通彩錦繡工藝恰好以在精細(xì)與豪放之間游刃有馀的簡(jiǎn)約形式,適應(yīng)了張仃的這種追求����。這次探望�����,她們還帶來最新繡製的張仃繪畫作品,以此作為緬懷并將在全國巡展�����?���;彝尢貏e提到張仃生前的一個(gè)未了心愿:“張老在世時(shí)就呼吁,中國工匠在藝術(shù)文化史上很了不起,中國美術(shù)史卻始終忽略了中國工匠的貢獻(xiàn)���,他一直希望補(bǔ)進(jìn)這一章��。他說過:‘不要只說工匠只有技術(shù)沒有藝術(shù)���;沒有藝術(shù)的再創(chuàng)造,沒有對(duì)藝術(shù)的深刻理解���,就創(chuàng)作不出傳世精品����。’”聽罷此言�,在場(chǎng)之人無不動(dòng)容�。
提攜后輩無分門第身份
今年多個(gè)紀(jì)念展中有一個(gè)頗為不同:河南省新鄉(xiāng)市舉行的“風(fēng)骨.紀(jì)念張仃先生誕辰100周年—竇憲敏山水畫藝術(shù)展”��。這是一名熱愛繪畫的農(nóng)民青年與大師不解之緣的延續(xù)與懷念���。二十多年前����,竇憲敏曾陪年事已高的張仃六進(jìn)太行寫生�����,這位大師級(jí)的藝術(shù)家還曾親臨他輝縣農(nóng)舍看畫指點(diǎn)��,老人欣賞的是年輕人的淳樸和幾分才氣��。機(jī)緣造就年輕農(nóng)民親近大師���,目睹其忘情山水的創(chuàng)作狀態(tài)。對(duì)于一個(gè)真正的藝術(shù)家來說����,寫生,不僅是為創(chuàng)作積累素材和訓(xùn)練基本功��,面對(duì)千變?nèi)f化的大自然�����,更是觸摸那份原始沖動(dòng)與天地直接對(duì)話的過程����。經(jīng)大師的提攜和鼓勵(lì)���,竇憲敏二十多年跋涉藝術(shù)之路終有所成�����,目前已是頗有名氣的專業(yè)畫家。他創(chuàng)作的最重要主題就是太行山��,因?yàn)檫@里不僅是他的家鄉(xiāng)�,而且是先生晚年藝術(shù)之變的重要載體���。竇憲敏近年新拓展用焦墨表現(xiàn)太行山特有的沉雄厚重,那是先生晚年所寄讬的深沉的審美況味���。親赴新鄉(xiāng)參加“風(fēng)骨”紀(jì)念展間隙����,年逾九十的灰娃又一次來到太行山,群山環(huán)伺睹景思人:日夜與自然親近�,是張仃生命的本真,進(jìn)入大山寫生,他始終懷有朝圣般虔誠�����。提攜后輩�����、扶助成才,先生更是從來無分門第與身份���。
灰娃是著名詩人����,從張仃晚年藝術(shù)思想的聆聽者��,如今成為深刻的解讀者����。自上世紀(jì)四十年代在延安相識(shí)到老年為伴,藝術(shù)和詩歌的聯(lián)璧輝映燦若永恒的生命伊甸園�。張仃畫筆下的灰娃高高髮髻,高雅華美����;灰娃詩行里先生則是“天意深植你一副惻隱敏感之靈性神把自己性靈附身與你”�?����;彝奚砑鎻堌晖砟甑?ldquo;生活秘書”和“工作秘書”���,守護(hù)先生走過了一生中安詳平和的最后二十五年�。她每日會(huì)將桌面上擺好魯迅的書�,沏好綠茶�,放上煙斗��;還會(huì)將宣紙摺疊成格,倒墨���、抻紙�����、鈐?����?;六進(jìn)太行�����,三赴甘肅�����,二進(jìn)秦嶺,登泰岳����,臨崑崙,上賀蘭��,下苗寨���,進(jìn)九寨……她十年間伴隨先生寫生的足跡����,幾乎把神州大地走遍�。盡管張仃晚年說話越發(fā)少,但說起話來卻是微笑的��,從心里透著歡喜���。據(jù)灰娃回憶���,先生也曾夢(mèng)中驚醒,那是歷史的浩劫所造成的痛苦穿透夢(mèng)境���。黯淡歲月里他以孤獨(dú)困惑而堅(jiān)定的韌性,用生命的尊嚴(yán)等待春天來臨�。即便是晚年的書法日課�����,他也喜歡用小篆書寫“故園不可見”��、“陽關(guān)第四聲”���、“搖落故園秋”等語句��,那就像張仃窮其一生守護(hù)的民族精神家園。
要守住中國畫筆墨底線
針對(duì)被忽視和輕慢的民間藝術(shù)�����,張仃言之灼灼:“我寧可欣賞一塊民間藍(lán)印花布,而不是欣賞團(tuán)龍五彩的宮緞����,民間藝術(shù)是不夠成熟,有時(shí)甚至粗野的�,但有清新之氣�����,自由之氣�,欣欣向榮之氣!”針對(duì)中國畫方向的迷失��,他大聲疾呼:“沒有中國畫的危機(jī)���,只有中國畫家的危機(jī)�!一方面,不抉擇探索�,就會(huì)有危機(jī)�;另一方面,脫離人民和生活�����,也會(huì)有危機(jī)����!”針對(duì)民間藝術(shù)理論研究的不足�,他尖銳指出:“學(xué)人的矇眬遠(yuǎn)比民眾的矇眬和民間藝術(shù)進(jìn)不了博物館�,更帶有悲劇色彩!”這些諄諄告誡猶如老人對(duì)中國藝術(shù)界的贈(zèng)言,今年在不同場(chǎng)合被反覆提及和引用����。張仃晚年還與多年老友吳冠中展開一場(chǎng)轟動(dòng)中國美術(shù)界、迄今仍有巨大影響的關(guān)于“筆墨等于零”的論爭(zhēng)����。張仃明確反對(duì)“筆墨等于零”�,他鮮明地指出:“筆精墨妙,這是中國畫文化慧根之所繫����,如果中國畫不想消亡�����,這條底線就必須守住���。但在這條底線上作業(yè)�,需要悟性��,更需要耐性�,急不得�、躁不得,更惱不得��,最后就是看境界�,看格,看品��。”青年畫家榮宏君在追憶文章中寫道:“‘筆墨等于零’的拋出����,使像我一樣的一些藝術(shù)青年陷入了沉思和彷徨����,正是張仃先生的這篇文章給藝術(shù)理論界打了一針強(qiáng)心劑����,堅(jiān)定了我們堅(jiān)持繼承祖先優(yōu)秀文化的決心和信心。今天重讀����,我依然認(rèn)為每一個(gè)有良知的美術(shù)工作者都應(yīng)該為先生的風(fēng)骨所感佩����!”
站在張仃先生《哪咤鬧?����!返乃囆g(shù)設(shè)計(jì)長卷前,一個(gè)五�����、六歲的小男孩牽著媽媽的手說個(gè)不停:“我喜歡哪咤���,我也喜歡我畫的龍王”���。稚語里透著天真的自信,小童可知道����,紀(jì)念展的主角—銀髮白鬚的老爺爺就是這部民族彩色寬熒幕動(dòng)畫片《哪咤鬧?���!返目傇O(shè)計(jì)�����。一九七八年改革開放之初,這位大藝術(shù)家將民間膾炙人口的神話里的哪咤加以藝術(shù)昇華��,于是幾代中國人所熱愛的動(dòng)畫形象誕生了�,并深刻影響著日后中國民族風(fēng)格的動(dòng)漫��。
文化自信源于民間藝術(shù)
張仃也始終懷有一種自信��,這就是以自己本民族的民間藝術(shù)為傲���。上世紀(jì)五十年代,他主持巴黎國際藝術(shù)博覽會(huì)中國館設(shè)計(jì)時(shí)���,曾去法國南部拜會(huì)過畢加索���,他將門神木版年畫和一本水印的《齊白石畫集》作為禮物帶給西方藝術(shù)大師���。文化的基礎(chǔ)追溯到民間�����,立顯廣闊和龐大�����。張仃曾指出:“民間的影響對(duì)我來說不僅僅是藝術(shù)層面的問題,更重要的是在精神層面�。我來自民間����,我始終認(rèn)為我是與人民聯(lián)繫在一起的,與他們的喜怒哀樂是感同身受的��。”清華大學(xué)美術(shù)學(xué)院教授鄒文認(rèn)為�����,張仃所有關(guān)于民藝的言論完整表達(dá)出這樣的觀點(diǎn):民間文化是中華文化最重要的資源內(nèi)涵�。在現(xiàn)代化全球化的文化境遇中,這可以被視為“一種根脈的自主”�����。其實(shí),不管做什么藝術(shù)���,張仃都主張符合人類理想���,因?yàn)楦徊赜诿耖g藝術(shù)的這種本原精神���,一直與人類對(duì)真、善���、美的追求�,同理同向。
二○一七年��,中國藝術(shù)界在問:張仃究竟給我們帶來什么�����、又留下什么���?灰娃說:“我其實(shí)并不愿意他就這樣成為一個(gè)歷史人物��,因?yàn)樗偸桥c時(shí)俱進(jìn)�,總是跟上時(shí)代�����,不喜歡依附�����,不喜歡僵化�����。在自然規(guī)律之下��,沒有誰能搶救張仃的生命,但是我們認(rèn)為如果張仃先生確實(shí)存在某種精神和價(jià)值的話�,那這種精神和價(jià)值才是應(yīng)該被搶救的����。”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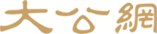








 京公網(wǎng)安備11010502037337號(hào)
京公網(wǎng)安備11010502037337號(hào)